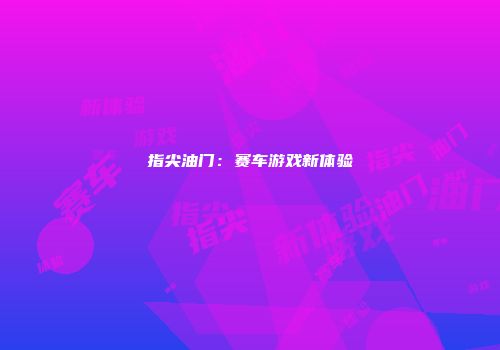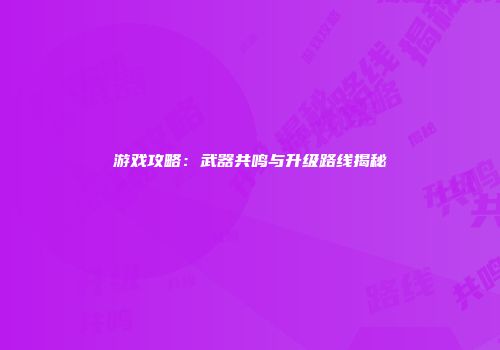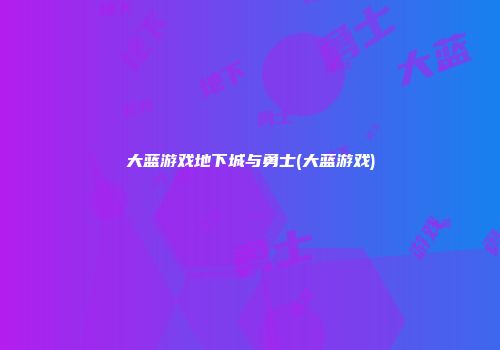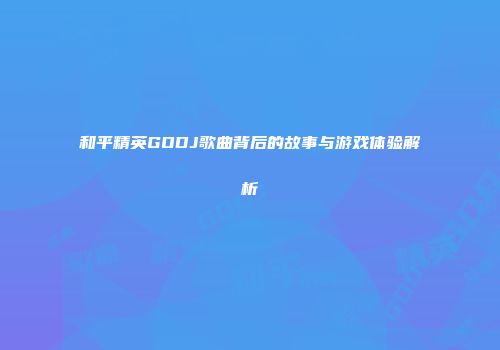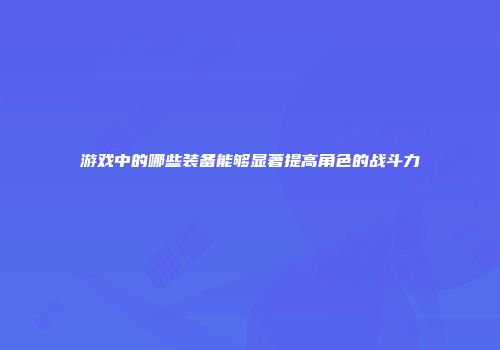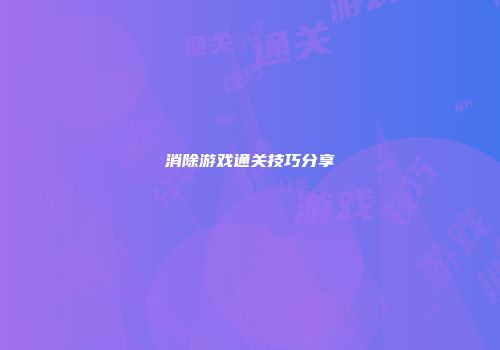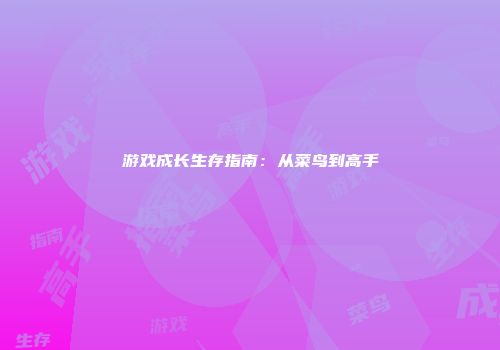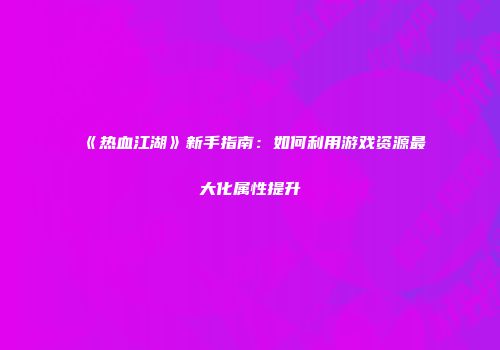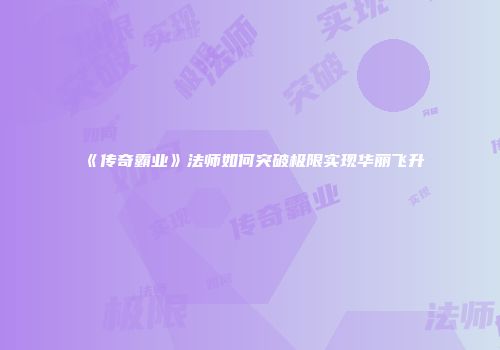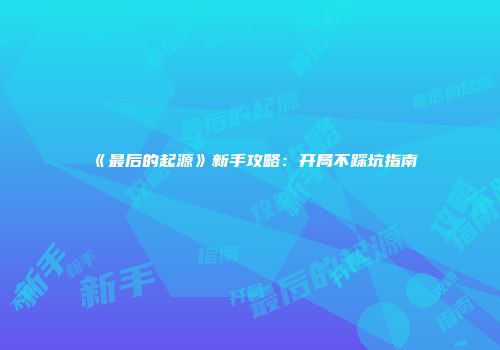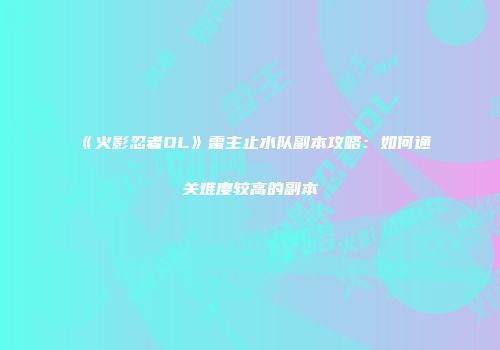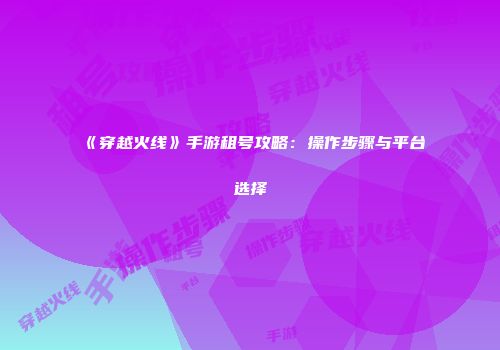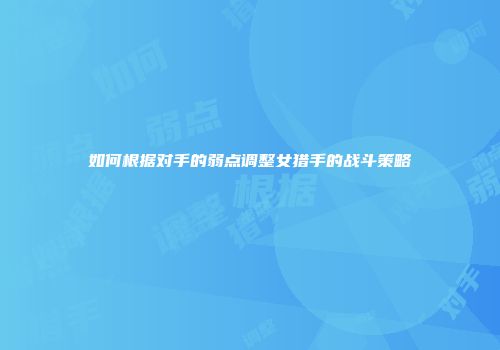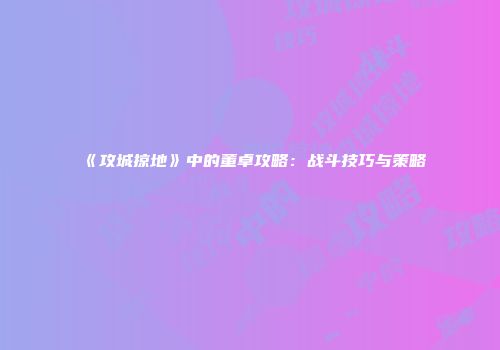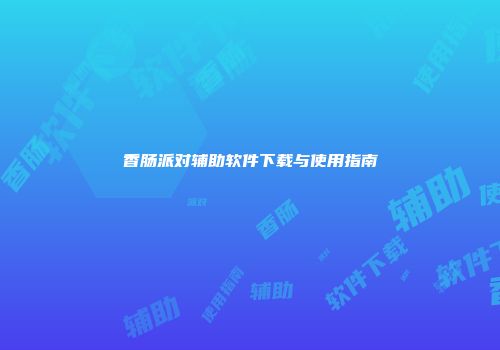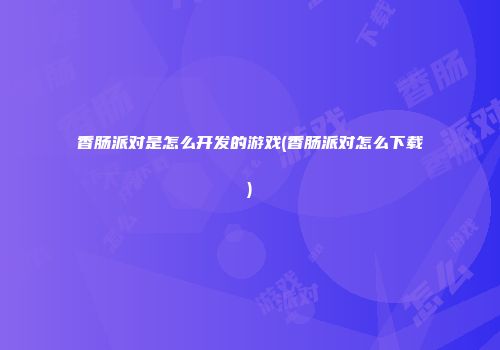纪念碑谷:解谜游戏背后的魔力与启示
 2025-09-28 06:15:41
2025-09-28 06:15:41
上周三深夜,我瘫在沙发上第18次重玩《纪念碑谷》,手指机械地滑动屏幕旋转楼梯时,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解谜游戏的痴迷早就超出了普通爱好。这种渴望像般刺激着神经——每次成功破解机关时的颅内高潮,发现隐藏线索时的会心一笑,还有卡关时抓耳挠腮的焦虑感,都让我欲罢不能。
解密新宠:这个叫Puzzle的游戏有什么魔力
新发现的Puzzle游戏像块磁铁牢牢吸住了我。区别于传统密室逃脱的套路,它的核心机制是「动态知识拼图」——每个场景都在教玩家新的思维工具,而这些工具会在后续关卡组合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- 在第一章「光影迷宫」里,我学会了用镜子折射破解激光阵
- 到第三章「时间褶皱」时,发现可以叠加之前的镜面技巧制造时间循环
- 最近卡在第五章「量子花园」,突然顿悟用三维投影解二维谜题
资深玩家私藏的4步破局法
| 阶段 | 操作重点 | 典型错误 |
| 观察期 | 360°环视场景,标记所有可交互元素 | 急着动手操作导致忽略环境暗示 |
| 联想期 | 建立元素间的拓扑关系图 | 被表面逻辑误导陷入思维定式 |
| 试错期 | 用沙盒模式验证假设组合 | 过度消耗资源导致后期被动 |
| 验证期 | 记录成功路径的因果链条 | 忘记复盘底层逻辑错失知识迁移机会 |
那些游戏不会明说的隐藏规则
经过37小时的鏖战,我总结出三条黄金定律:
- 悖论优先原则:当所有常规解法都失败时,违反直觉的操作往往暗藏生机
- 视觉陷阱防御:特别注意重复元素的数量变化和比例失调
- 动态难度补偿:连续失败5次后,场景会隐晦增加提示光效
资源管理比智商更重要
上周三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:在「混沌图书馆」关卡挥霍了所有放大镜次数,结果面对需要同时观察四本书的终极谜题时,只能眼睁睁看着线索模糊成马赛克。现在我养成的新习惯是:
- 每次使用道具前默念「三问法则」:
- 这是唯一时机吗?
- 是否有替代方案?
- 后期会不会更需要?
- 建立「道具能量表」优先级系统
现实世界的意外收获
最惊喜的是游戏思维正在改变我的生活决策方式。上周帮邻居找走失的猫咪时,下意识应用了场景分析法:
- 绘制社区三维地图标注所有藏匿点
- 根据猫咪习性建立移动路径模型
- 用食物诱饵设置动态监测点
结果两小时就在废弃车库找到了那个毛茸茸的小逃犯。这种将虚拟训练转化为现实能力的过程,就像突然获得超能力般令人着迷。
当卡关成为修行
现在面对看似无解的难题时,我会泡杯正山小种,打开专门准备的「灵感手账」。最新发现是凌晨三点的大脑最具创造力——有次在半梦半醒间突然想通「镜像对称」关卡的解法,抓过手机一试竟然成功,那种茅塞顿开的堪比第一次解开魔方。
窗外的晨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画着光栅谜题,咖啡机发出蒸汽喷涌的声响。保存好刚攻克的「拓扑监狱」进度,我知道明天等待着的又会是全新的思维挑战。书架上的《哥德尔、艾舍尔、巴赫》在台灯下泛着暖黄的光,或许该重读那章关于自指悖论的论述了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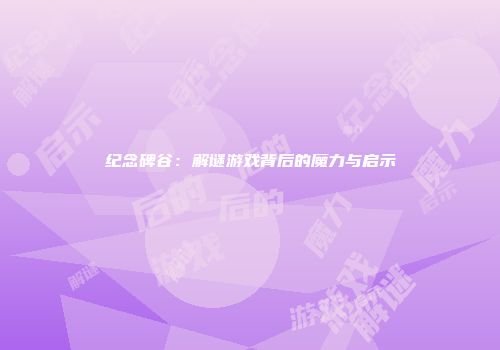
郑重声明:以上内容均源自于网络,内容仅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或者公益分享,非商业用途,如若侵犯到您的权益,请联系删除,客服QQ:8411441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