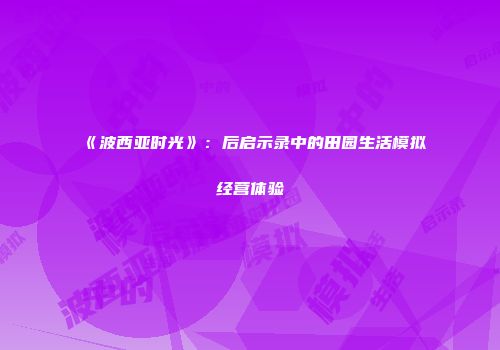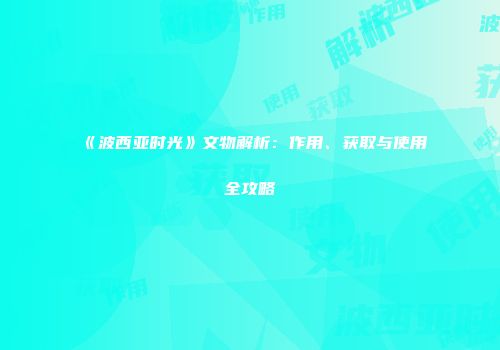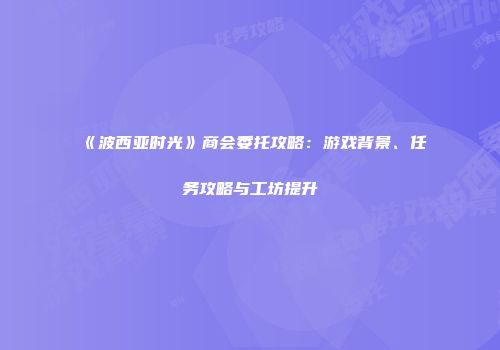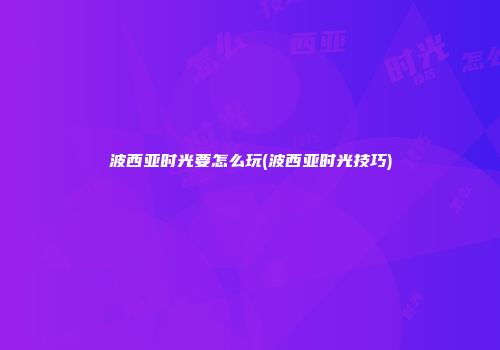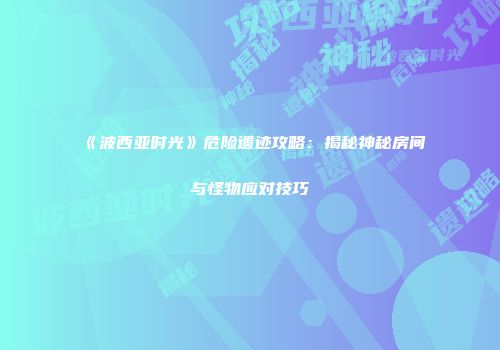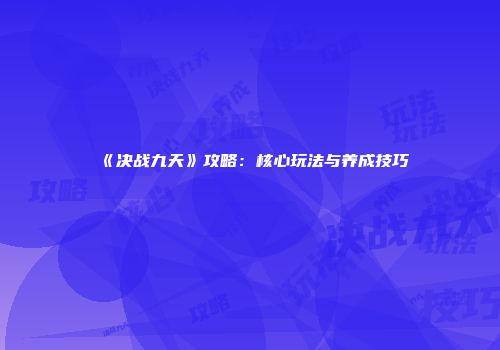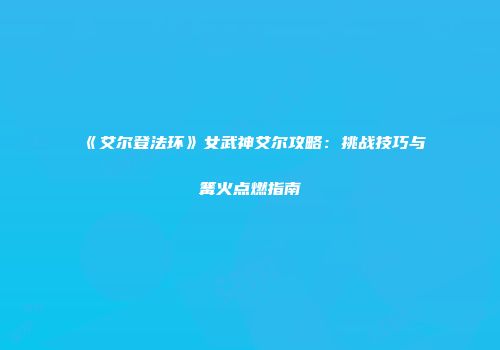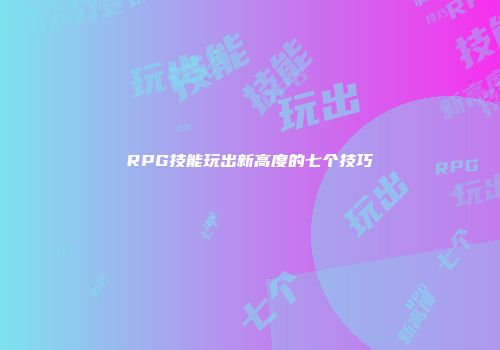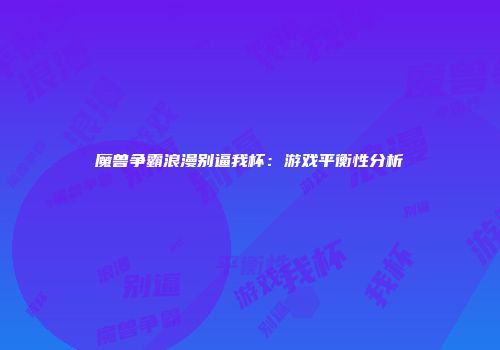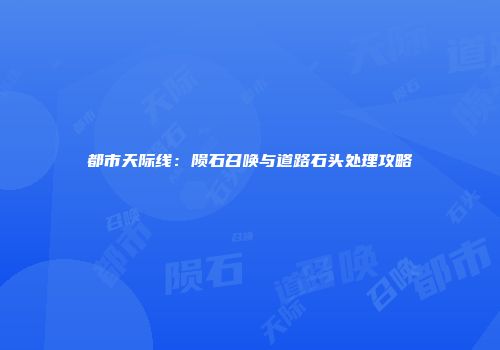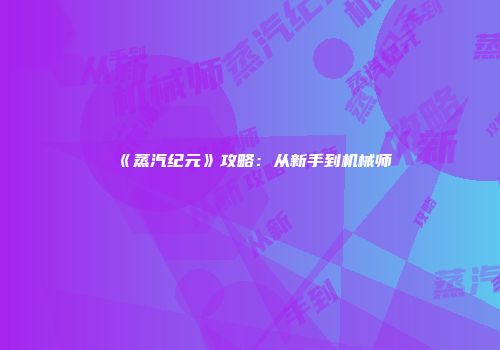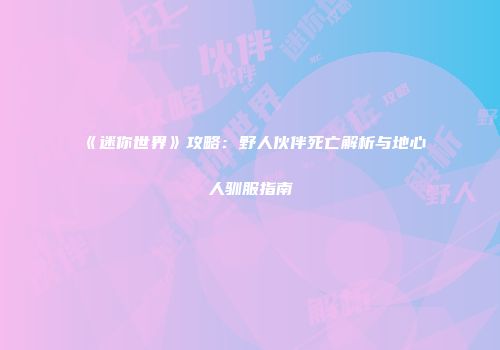雾山村记忆:童年时光与自然馈赠
 2025-07-12 03:17:34
2025-07-12 03:17:34
山道拐过第七道弯时,我看见了那棵歪脖子老槐树。树皮上深深浅浅的刀痕还是老样子,最上面那道豁口是我十二岁那年用柴刀砍的——当时为了摘树梢的野柿子,差点摔断腿。树根处新添了半截红布条,在山风里扑簌簌地抖,像是雾山村在朝我招手。
初遇雾山
2008年暑假,跟着地质队工作的父亲进山,卡车在盘山路上颠了六个钟头。十岁的我趴在车窗上,看见远处青灰色山峦间浮着奶白色的雾带,“那是雾山的腰带,系着整个村子的命脉”,开车的陈师傅往窗外啐了口槟榔渣。
- 第一印象:青石板路硌得球鞋底发麻,屋檐下的腊肉泛着油光
- 意外收获:村口杂货铺的麦芽糖用芭蕉叶裹着,甜里带着草木香
- 永恒画面:吴婆婆踮着小脚追芦花鸡,鸡毛粘在她藏青色围裙上
山里的日子
跟着放牛娃阿旺钻竹林那周,我学会了辨认三十多种野菜。他总能把细竹枝折成口哨,吹着不成调的《刘三姐》。我们在溪涧逮到的石斑鱼,用湿芭蕉叶裹着埋进炭火,鱼鳞在高温下卷成金黄色的脆壳。
| 2008年 | 泥坯房占80% | 主粮:玉米、红薯 | 交通工具:骡子 |
| 2018年 | 砖混结构房65% | 经济作物:山茶油 | 村道通小巴 |
雾的馈赠
雨季来临前的晨雾最是浓稠,像化不开的藕粉。跟着采药人老孙头进山,他的竹篓里永远装着三种宝贝:包着烧酒葫芦的油纸包、磨得发亮的铜烟锅,还有用红绳系着的《本草图鉴》手抄本。

雾中三珍:
- 云雾茶要在日出前采下带露水的芽尖
- 石耳生长在背阴崖壁,采摘时得系麻绳
- 野山蜂巢藏在老樟树洞里,取蜜得用松明熏
老祠堂的钟声
2015年清明返校前夜,村里祭祖的铜锣声惊醒了我。月光透过祠堂的雕花窗,在青砖地上投下菱格纹的影子。守夜的六叔公往我手里塞了块艾草糍粑,“后生仔多吃点,长得比祠堂的杉木梁还结实”。
四季轮回
这些年断续记录的天气本子,页脚都卷成了波浪形。霜降后的清晨最适合收集松针露,用粗陶罐接了煮茶;夏至时节的雷雨来得急,但晒谷场的老人们总能提前两炷香时间收完花生。
最后一次见阿旺是在前年开春,他新买的拖拉机突突冒着蓝烟。“后山要建气象站哩,你教我的温度计用法可算派上用场”,他指甲缝里还沾着修理机车留下的黑油泥,笑起来还是露出那颗被山核桃崩缺的犬牙。
山脚的野柿子林今年结果特别密,沉甸甸的压弯枝桠。回程时背包侧袋插着吴婆婆硬塞的酸萝卜罐子,玻璃瓶身上凝着细密水珠,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似的光晕。中巴车发动时,我听见有人在后山梁子上吹竹哨,调子依稀是当年没学全的《刘三姐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