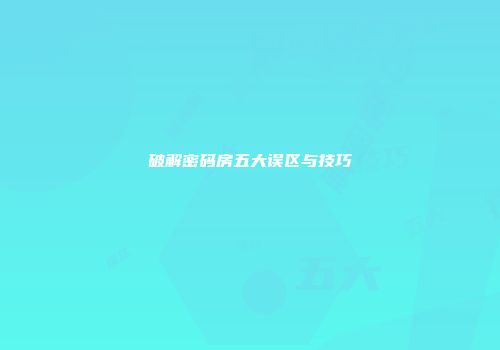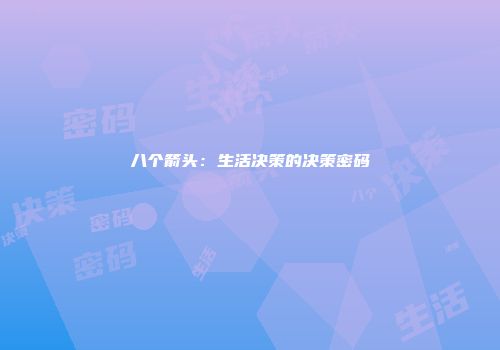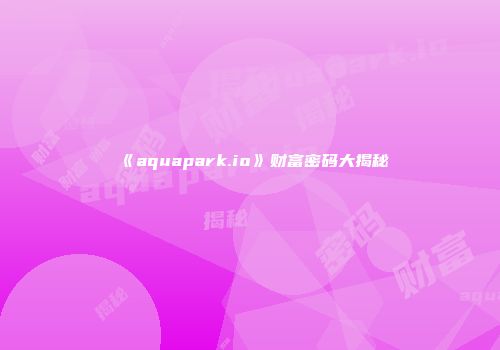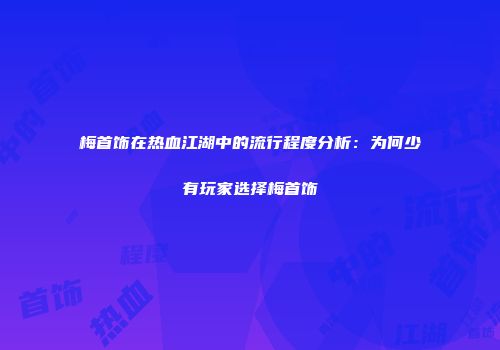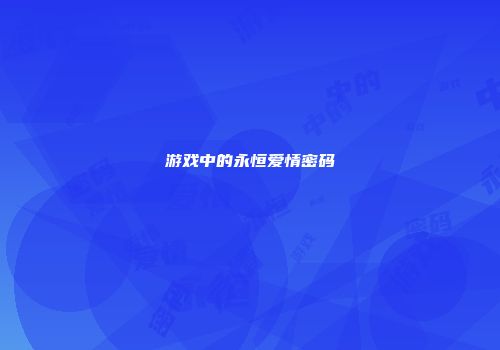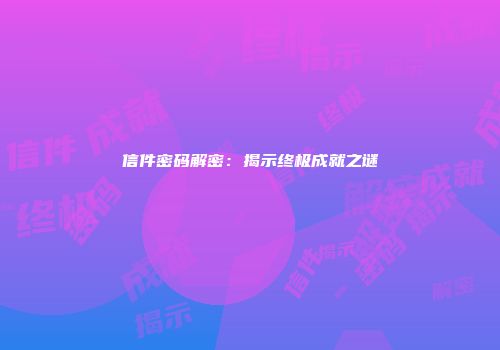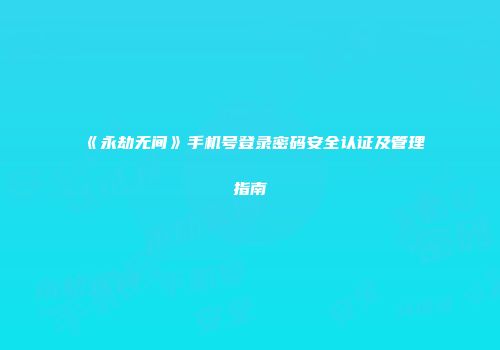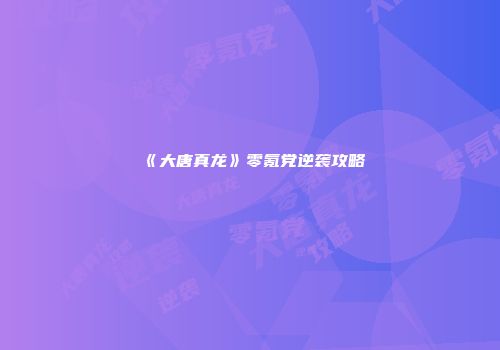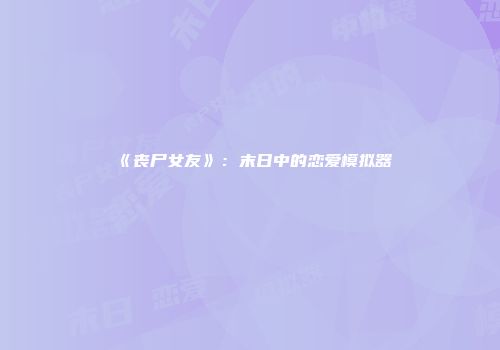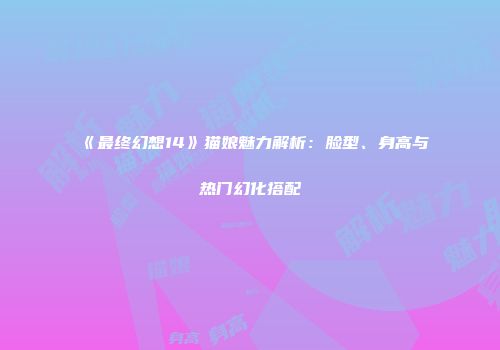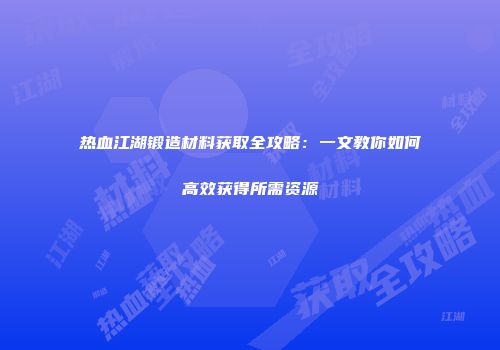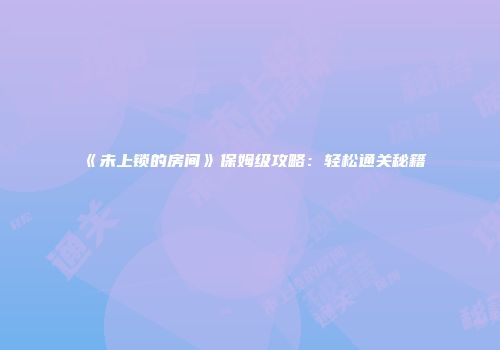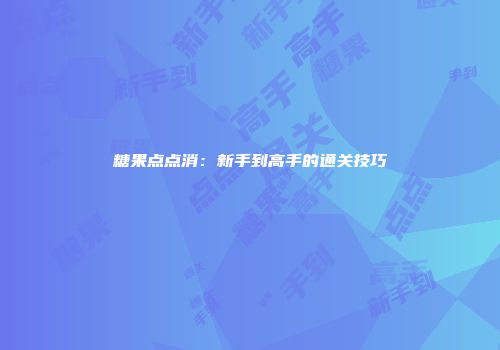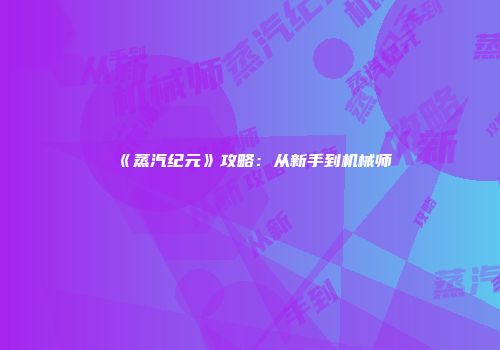古韵首饰:礼仪与审美密码
 2025-07-20 06:23:32
2025-07-20 06:23:32
清晨的阳光穿过雕花窗棂,照在铜镜前梳妆的仕女身上。她小心地将金步摇发髻,又取下襟前玉璜系在腰间。这些动作里藏着两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——衔与佩带。就像我们现在分不清"戴戒指"和"套戒指"的微妙差异,古人在首饰穿戴方式上的讲究,正折射出礼仪之邦的独特审美。
齿间流转的文明密码
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蝉,表面有长期摩擦的痕迹。考古学家发现,这些本该佩戴在腰间的玉饰,很多都出现在墓主人口腔位置。原来商代人相信,把玉器衔在口中能让灵魂不灭。《礼记》记载的"琀玉"习俗,正是这种生死观的延续——贵族下葬时,口中必定要含玉蝉。
- 新石器时代: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骨哨,既作饰品又兼实用功能
- 战国时期: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16节龙形玉挂饰,每节都可单独衔咬
- 唐代壁画:侍女为贵妃整理妆容时,常用银簪衔住散落的发丝
腰间摇曳的礼制图谱
走在长安东市,你能通过腰间的玉组佩判断行人身份。三公九卿的组佩长度及膝,士人仅到胯部,平民则禁止佩戴玉饰。这种佩带制度在《周礼》中有详细规定:天子佩白玉,公侯佩山玄玉,大夫佩水苍玉。最有趣的是组佩的声响规制——身份越高,玉器相撞的"璆锵"声越清越,成为移动的礼仪教科书。
| 对比项 | 衔 | 佩带 |
| 主要材质 | 玉、骨、贝 | 玉、金、银、丝绦 |
| 使用场合 | 祭祀、丧葬、巫术 | 朝会、宴饮、日常 |
| 象征意义 | 通灵、镇魂、祈福 | 身份、德行、审美 |
| 存续时间 | 新石器时代至汉 | 商周延续至清 |
发簪上的秘密语言
唐代女子及笄时,母亲会送一支合欢簪。这种发簪两头雕着鸳鸯,平时分开佩带在发髻两侧,成婚当日才合二为一。而在民间,银匠会在簪尾暗刻花纹——三道波纹代表待字闺中,缠枝纹暗示已有婚约。这些藏在佩带方式中的隐喻,比现在的社交软件状态更含蓄风雅。
《天水冰山录》记载严嵩被抄家的首饰清单里,"衔珠金凤"与"佩玉禁步"分列两类。前者是后妃在正式场合需轻咬以示端庄的特殊头饰,后者则是限制步态的礼仪佩饰。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这些文物,仿佛能听见环佩叮当声中,那些消逝在历史里的生活韵律。
工匠指尖的温度
明代金匠记录本里有个细节:制作衔口器物的工匠要斋戒三日,因为要接触"通灵之物";而打造佩饰的工匠则可以边干活边哼小曲儿。这种差别对待,源自古人认为衔器承载着连接阴阳的使命。苏州博物馆藏的宋代金蝉,口中机关至今仍能开合,让人惊叹当年匠人把实用与信仰结合的精妙。

红楼的丫鬟们给探春整理妆奁时,总要特别提醒:"姑娘的虾须镯得衔着戴"。这种金丝编成的镂空手镯,正确戴法是要用牙齿轻轻咬住活扣再转腕佩戴。贵族女子从小就要练习这种特殊的佩戴技巧,既防丢失又显仪态。如今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随手一套,倒是失了古人的那份讲究。
夕阳把老银匠铺子的柜台染成蜜色,陈列的仿古首饰中,一支累丝金簪反射着微弱光芒。不知哪位姑娘会买去,学着古人的样子,轻轻衔住簪头,把四百年前的月光别在发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