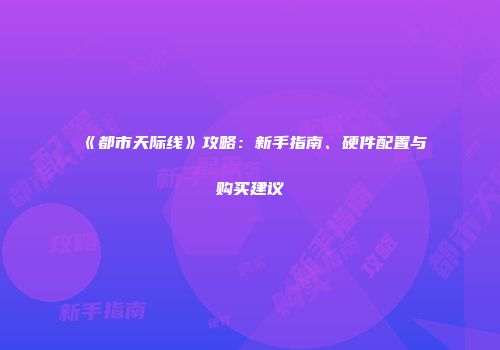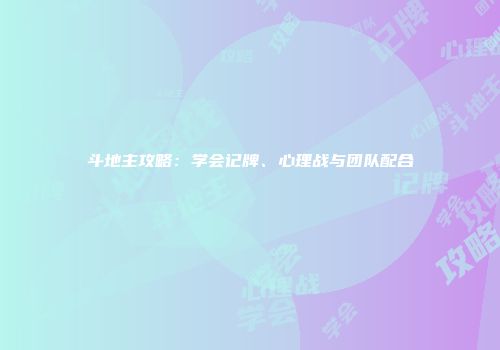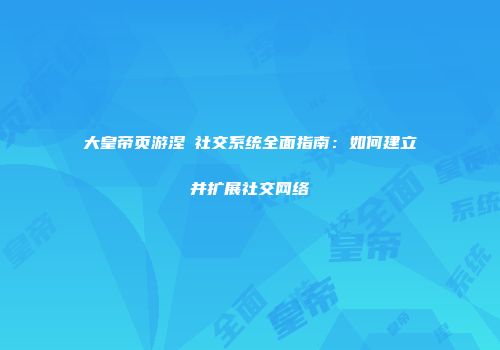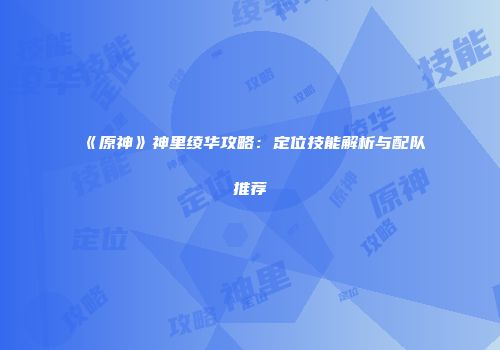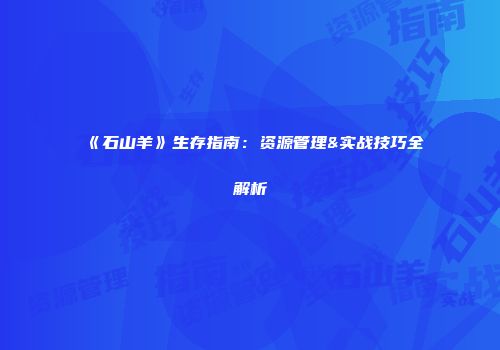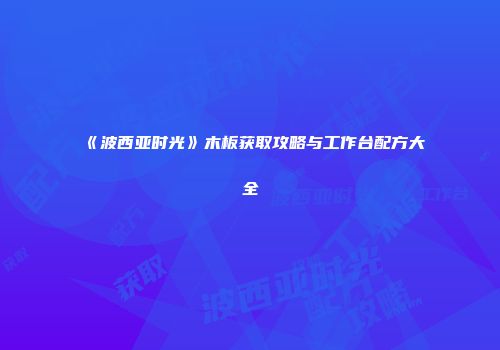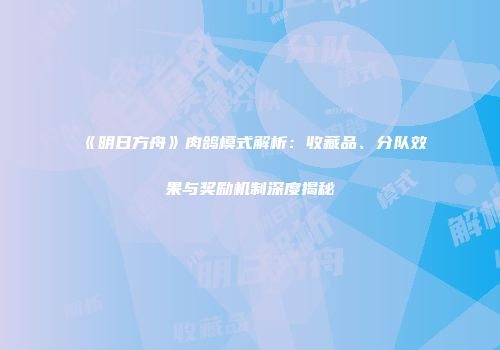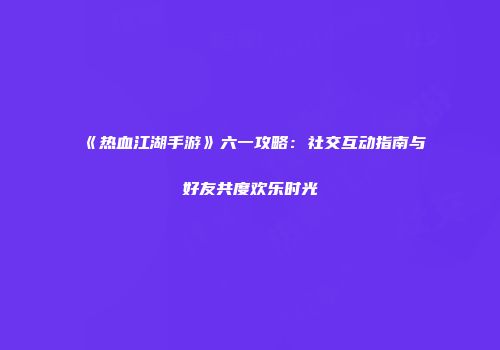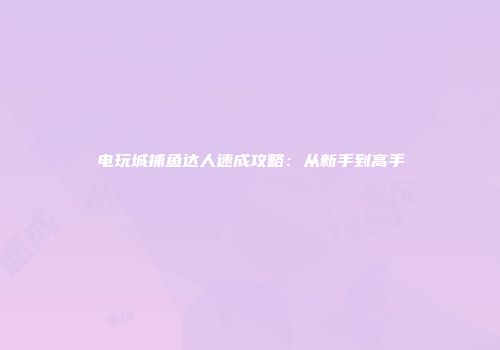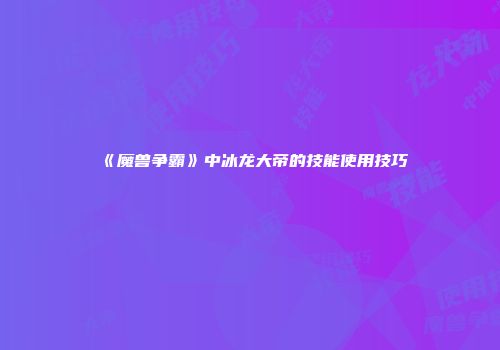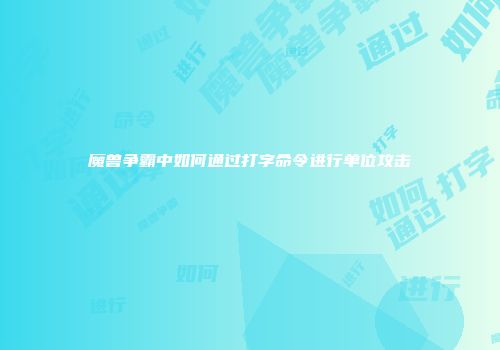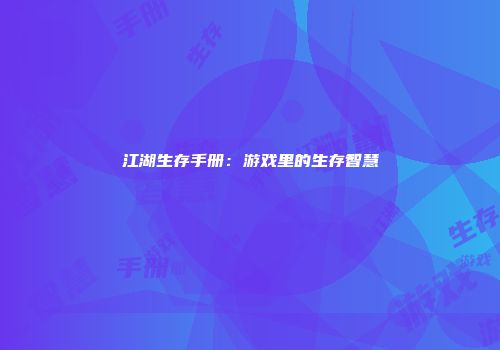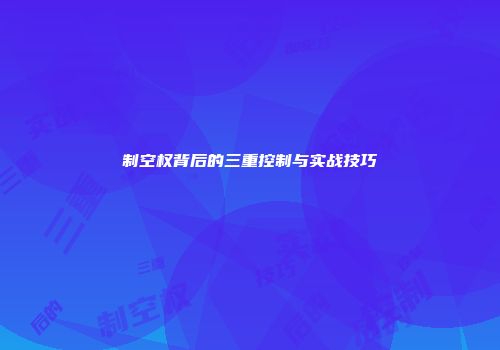暖气管烫伤启发的哥特文学创作
 2025-08-12 03:12:45
2025-08-12 03:12:45
去年冬天,我在二手书店翻到一本泛黄的《哥特文学史》时,手突然被暖气片烫了下。这个巧合让我决定写点"不太一样"的东西——于是有了现在这篇文字里的故事,它像块浸了墨水的海绵,沉甸甸压在读者胸口。
一、从暖气管烫伤开始的创作
我的老式铸铁暖气片在零下十二度的北京清晨,用一道三厘米长的灼痕叫醒了装睡的我。当时正卡在第六章:男主角该不该把捡到的流浪猫做成标本。皮肤传来的刺痛突然让我想通——真正的黑暗不是血腥画面,而是人在善恶临界点的本能选择。
- 凌晨三点反复修改的七版开头
- 采访殡仪馆化妆师得来的细节
- 故意拆掉所有感叹号的电子草稿
1.1 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绝的初稿
有位编辑在退稿信里写:"你让反派在杀人前背《小王子》段落,这比直接描写残肢更让人毛骨悚然。"这恰好印证了我从《沉默的羔羊》里学到的技巧:用美好事物作对比,黑暗会更浓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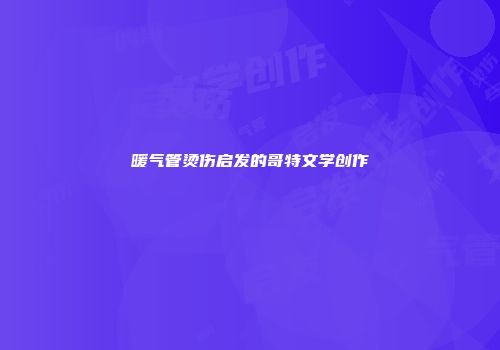
二、那些在咖啡渍里成形的人物
| 角色 | 原型碎片 | 最终变异 |
|---|---|---|
| 药剂师林夏 | 社区医院总忘戴老花镜的配药阿姨 | 能用眼药水调配吐真剂的退休特工 |
| 流浪少年阿九 | 总在小区翻垃圾箱的橘猫 | 携带远古寄生虫的"人形载体" |
常去的咖啡馆老板有次打趣:"你总盯着客人沾在杯口的唇印看,该不会在选谋杀目标吧?"他无意中说中了我的素材收集法——观察普通人最松懈的瞬间,那里藏着未被驯化的本性。
2.1 让角色自己生长的秘诀
写到四分之三处,法医女主突然在雨夜给凶手递了伞。这个脱离大纲的举动,反而让后期审讯室的攻防战有了火药味。就像《绝叫》里的阳子,当人物拥有真实呼吸,故事就会挣脱作者掌控。
三、水泥森林里的恐怖美学
- 地下车库的应急指示灯比墓地磷火更瘆人
- 外卖app的"准时达"倒计时像定时炸弹
- 业主群里要求处死流浪狗的投票
有读者在豆瓣书评里说:"最恐怖的是发现自己在同情食人魔。"这让我想起写超市冰鲜柜场景时,冷气顺着键盘爬进指关节的凉意。现代社会的规整秩序下,压抑的疯狂才更具杀伤力。
| 传统恐怖元素 | 都市化改编 |
|---|---|
| 古堡蝙蝠 | 写字楼玻璃幕墙上的飞鸟撞击痕 |
| 女巫药水 | 网红减肥茶包里的致幻蘑菇粉 |
四、藏在致谢名单里的彩蛋
最后页的鸣谢中,"特别感谢总在凌晨两点施工的邻居",其实对应着书中关键的分尸案音效描写。有位眼尖的读者发现,全书章节数正好是北京地铁末班车时间——23:15,换算成23章15小节。
现在敲着这些字,窗外的春雨把玻璃晕染成毛玻璃。新书已经在写,主角是位总在阴天犯关节痛的退休刑警。他养了盆总也开不了花的昙花,阳台上能看到对面楼的电梯指示灯明明灭灭。
郑重声明:以上内容均源自于网络,内容仅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或者公益分享,非商业用途,如若侵犯到您的权益,请联系删除,客服QQ:8411441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