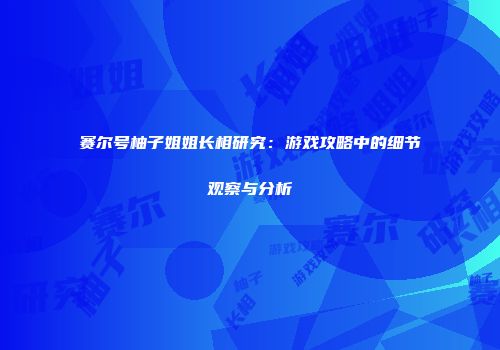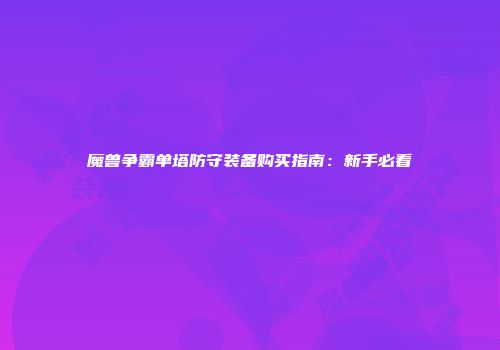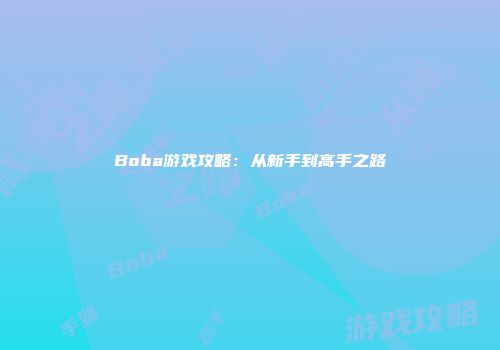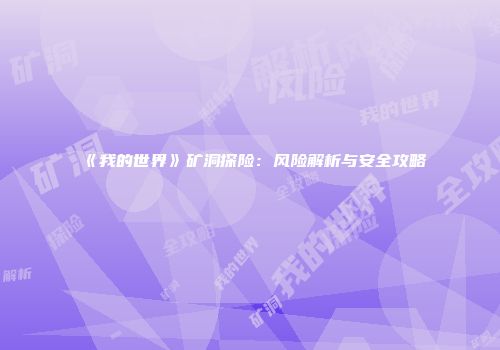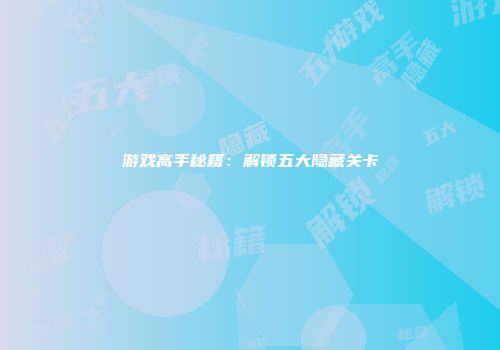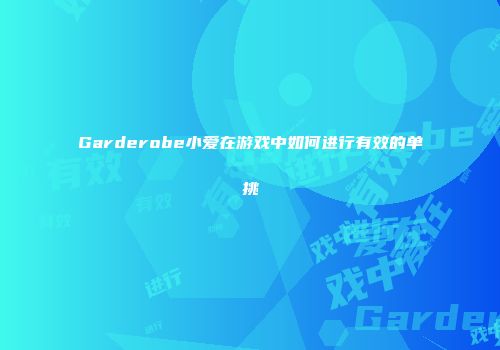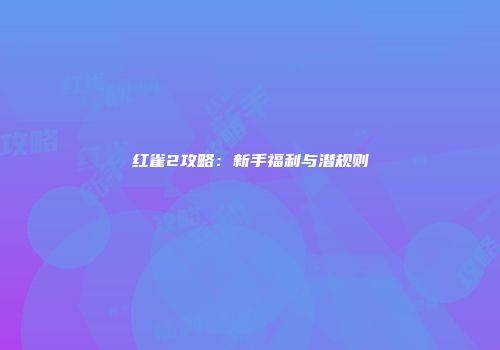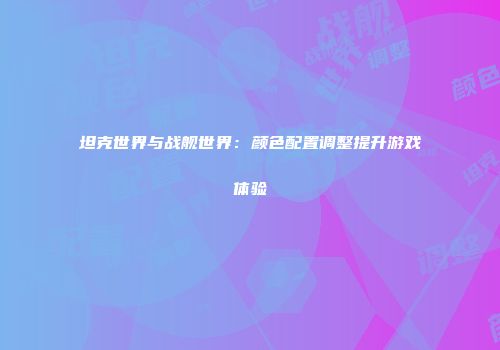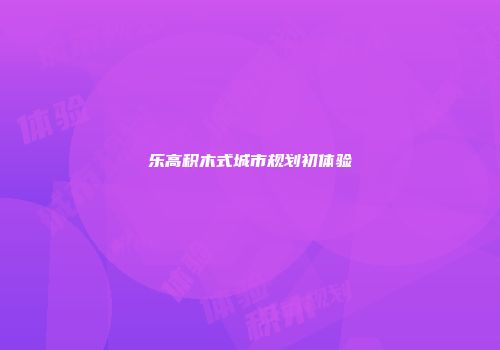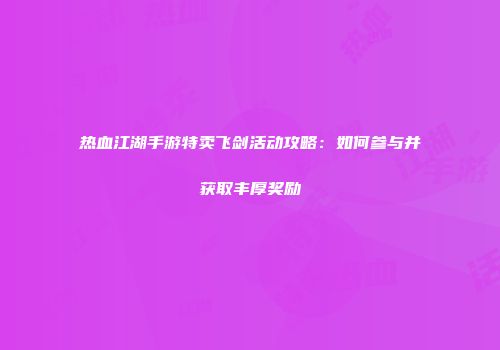深灰毛衣下的市政诗人
 2025-09-27 10:25:53
2025-09-27 10:25:53
每天清晨五点半,书房台灯准时亮起。父亲套着磨出毛边的深灰毛衣,在实木书桌上铺开稿纸,钢笔尖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会持续两小时——这是他雷打不动的创作时间。作为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区长,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二十三年。
公文包里的秘密
区政府司机老张有次和我打趣:"你爸的公文包总比别人沉三斤。"确实,那个黑色牛皮包里永远躺着两本书: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和最新版《城市规划条例》。在陪同考察老旧小区改造的间隙,他会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,记下突然迸发的灵感。
- 1999年:发表中篇小说《梧桐巷记事》,原型是负责棚户区改造时遇到的钉子户老人
- 2008年:长篇小说《钢筋森林》获省级文学奖,描写新城扩建中的官商博弈
- 2021年创作高峰期:利用防疫值班时间完成12万字《疫线笔记》手稿
文字与混凝土的化学反应
城建局的李叔告诉我,父亲主持设计的滨江文化长廊方案,最初竟是写在小说草稿背面的。那些蜿蜒的亲水步道位置,对应着他某部作品中主人公的逃亡路线。"既要让推婴儿车的母亲走得舒服,也得让流浪猫有地方晒太阳。"这是他在方案评审会上说的原话。
| 文学主题 | 对应市政工程 | 社会反响 |
| 《夜巡者》城市孤独症 |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| 夜间使用率超65% |
| 《菜市口》市井文化 | 传统集市改造 | 保留78%原摊主 |
| 《桥》两岸隔阂 | 跨江步行桥 | 成为网红打卡点 |
书房里的市政厅
母亲总抱怨家里书房像个建筑工地:墙上钉着城区卫星图,书柜里《百年孤独》和《给排水工程设计手册》肩并肩,窗台上堆着各色石头——都是父亲从工地带回来的混凝土样本。去年旧城改造时,他连续三周把拆迁户请到家里喝茶,那些录音对话后来变成了纪实文学《茶渍》里的章节。

凌晨两点的创作法则
- 用毛笔批文件:强迫自己放缓阅读速度
- 录音笔不离身:收录市井声音作写作背景音
- 反向创作法:先设计小说结局,再倒推现实解决方案
记得有次暴雨夜,父亲突然冲进我房间借运动相机。原来新建的下穿隧道出现积水,他要去现场勘查,顺便记录水流浪花形态。"这段写暴雨场景用得着",浑身湿透回来时,他手里的相机还在滴水,眼睛却亮得吓人。
菜市场的文学沙龙
周末陪父亲买菜是全家保留节目。他在豆腐摊前能和老板聊半小时,从点卤工艺引申到传统手艺传承。卖水产的老王头是他忠实读者,总用草绳捆着活鱼递过来:"新书里那个养锦鲤的处长,原型是水务局老刘吧?"
这些鲜活对话最终都会出现在他的市政会议记录里。上个月的城市亮化方案讨论会上,他突然背诵起自己小说里描写霓虹灯的一段,整个会议室安静了十秒钟。后来方案调整,减少了40%的LED光带。
窗外的梧桐叶飘落在摊开的《城市美学》上,父亲摘下老花镜,往我的茶杯里续了热水。远处工地的打桩声隐约传来,和书房里的挂钟滴答声渐渐混成某种特别的韵律。